故事一
一个开设死亡课的女护士
余芹是解放军总医院生物治疗科的一名护士,她这里的病人多数是复发难治、肿瘤晚期的患者,正因为如此,余芹看多了生死。
她发现,患者家属在医疗决策中往往占据主导地位,在面对生命垂危的亲人时,家属们常常选择气管插管、使用呼吸机等手段一味维持亲人的生命,事实上,很多时候这些仅仅是维持着亲人的生命体征,不但对治疗没有丝毫作用,还让自己的亲人离世时十分痛苦。
“这样做对于患者而言究竟是延长了他们的生命,还是增加了他们的痛苦,是尊重了他们的生命,还是仅仅满足了家属们的情感需求?”每次送走这样的患者,余芹总是在思考。
余芹所在科室的医护人员针对临终患者家属开展了一项研究,先选取临终状态患者的直系家属20人进行死亡教育,这些家属均自愿参加、能够配合调查、具有文字理解能力。在教育前使用“照护临终患者态度量表”对进行干预的患者家属进行评估,根据量表得分将照护临终患者态度分为三类:正向、中性、负向态度。
余芹说:“照护临终患者态度量表”适用于临终关怀及死亡教育等领域对于照护临终患者态度的测量,已被美国63所高校和另外8个国家使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在量表收回后,医护人员采用了沟通与讲座的形式对患者家属开展死亡教育,理论课程涉及“死亡及死亡教育概论”、“如何协助患者面对死亡”、“濒死患者的护理及生命最后旅程的规划”等内容。
第一节死亡教育理论课上,讲课的医护人员帮助这些患者家属加深对“生命的有限性”这一问题的理解,让他们从心理上接纳“死亡为生命一部分”的事实,消除他们对死亡的恐惧,坦然面对亲人的逝去,让他们能更加珍惜生命,热爱生活。
第二课让家属知道如何让患者在剩下的日子里活得无痛苦、有尊严;第三课是关于濒死患者的护理;第四课是关于生命最后旅程的规划。
在死亡教育的全部课程结束后,这些照护临终患者的家属填写了一份调查问卷,余芹和同事们发现,上完课的家属正性态度有了极大提高。
余芹印象深刻的一位有着绘画特长的患者,重疾在身但心态乐观,多次表示自己不愿接受临终前无谓的抢救。看到有的病友情绪低落,就号召家属们捐书,在病区里成立了图书角,并经常画一些绘本放到护士站,鼓励病友们正视病情笑看生死。
“当然也有例外”,余芹坦言,特别是有的患者比较年轻,家属们接受不了亲人即将离去的事实,总希望医生们再加一些手段,但很多时候都是徒劳的,只会增加患者痛苦,“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为什么不能让他们走得更舒服一些呢。”
“如果把生命比作一段旅程,我们现在做的是在旅程快接近终点时,才告诉大家如何去迎接终点的到来,因此能做的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我们应该在登上这段旅程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学着去迎接终点,这样不仅可以更从容地面对终点到来的那一刻,也会更懂得如何将这段有限的旅途走得更精彩。”余芹和同事们现在正努力将这个工作持续开展下去。
故事二
推广“尊严死”的将门之后
罗点点是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小女儿,做过多年医生的她在几年前和朋友们一起创办了“选择与尊严”公益网站,推广“尊严死”概念,并推出了我国首个民间“生前预嘱”文本。
“生前预嘱”是人们在健康或意识清楚时签署的,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的指示文件。“生前预嘱”中的“我的5个愿望”是罗点点参照美国的经验,为中国人做出的第一份生前预嘱样本,凡是年满18周岁的人都可以在“选择与尊严”网站上填写。这5个愿望分别是:在生命末期需要什么样的医疗服务、要不要使用心肺复苏和呼吸机等生命维持系统、在情感上需要别人如何对待自己、希望家人和朋友如何看待自己的死亡、谁来做我签署这份文件的见证人。每个人都可以登录“选择与尊严”网站,自愿填写“生前预嘱”,这些资料将永久保存在网站数据库中,如果想法变了,随时可以修改和撤销。
“死”历来是中国人最忌讳的字眼,这注定推广“尊严死”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罗点点和志愿者去各大医院传播“生前预嘱”,常常被医院的负责人婉拒:“我们这儿是救死扶伤的地方,谁接受得了你们说死呀!”她让朋友在公园里发问卷调查,退休的阿姨们不乐意了:“活得好好的,这么早让我们想到死?”
“签署‘生前预嘱’需要很大的勇气,所以要给大家时间,慢慢去接受这件事。”罗点点希望借鉴美国和香港等地的成功经验,再结合我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特点,让更多的人了解“尊严死”这个概念。
以93岁高龄去世的开国上将张爱萍将军的夫人李又兰,曾欣然填写生前预嘱:“今后如当我病情危及生命时,千万不要用生命支持疗法抢救,如插各种管子及心肺功能启动等,必要时可给予安眠、止痛,让我安详、自然、无痛苦走完人生的旅程。”后来老人实现了她的意愿,安详离世。
罗点点后来又推动成立了“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现协会的理事长为陈毅的儿子陈小鲁。陈小鲁加入这个团队,很大原因是他当年没能替父亲做出解脱痛苦的选择。临终时,父亲已基本没有知觉,瘦得不成人形的身上插满管子,靠呼吸机、输液和强心针维持。陈小鲁看得难受,却又不能也无力阻止。
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中心前主任刘端祺一直关注着“选择与尊严”网站的发展,作为治疗恶性病的临床医生,他见证了太多的死亡和无谓的过度抢救。
“有时该和病人说实话的时候就得说,有个病人不管家里的经济情况,想尽办法就为了能多活一会儿,一年内光是买机票到全国各地求医就花了十几万元,这时候就要提醒他,很可能这会是人财两空、同归于尽。尽量让医生和病人之间知识对称,最后的决定权在患者手里。”在刘瑞祺看来,尊严死绝不是“安乐死”,它只是不人为地延长自然的生命,是生命的自然终结。其实,当一个人的生命走到尽头时,他用什么样的方式离开人世,反映了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高低。
故事三
畅想过自己死亡的医学博士
吴海云,医学博士,解放军总医院老年心血管病研究所医生,从事临床工作近30年。作为医生,看惯生死,吴海云曾“畅想”过自己的死亡:我希望自己最后告别的过程,不要太长,不要花费太多的医疗资源。我希望尽可能呆在自己的家里,或者,如果比较幸运,呆在一个明亮、温馨的临终关怀机构里,而不是呆在陌生的,如同流水线工厂的医院里,在冷漠的机器和机械的程序里,告别这个世界。
在吴海云看来,死亡已成为一个越来越艰难的过程。现代医学建立了“重症监护室”,发明了种种复杂的生命维持系统。医生们要尽职尽责,“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百分之一百的努力”。
他的一个近80岁的病人,得了肺气肿、肺心病、呼吸衰竭、肺性脑病,临终前昏迷不醒,依靠呼吸机和插满全身的各种管子维持了两个月。有一天,心电监护仪报警,显示“心室颤动”。子女们恳求医生尽一切力量抢救。吴海云先是给病人做心脏电除颤,三次之后,监护屏上混乱的颤动变成为一条直线。然后医生们又开始了两个多小时的“胸外心脏按压”。
“当时我感觉到她的肋骨在一条条折断,在我的手底下摩擦。我们给她的静脉里,气管里,心室内,注射进各种药物。医生急切地喊着医嘱,护士们敏捷地执行,仔细地记录……子女们在满怀希望地等待着现代科学的奇迹。我不知道,这位操劳一生的可敬母亲,在想着什么。或许,如一些介绍濒死体验的文章所描述,她的精神已飘浮到了我们的上空,正在困惑地俯视着我们这些徒然忙碌的人群。”
吴海云说,自己参与过数以百计的终末期病人的“心肺复苏”,但从未见过一例成功的“起死回生”。只能说,这是现代医学特有的一种仪式。
吴海云说,自己不希望这样作最后的告别。
“根据预测,如果不出意外,我将死于癌症,很可能是肺癌。我希望自己的死亡过程不要太长,不要花费太多的医疗资源。除非会给家人带来难以承受的负担,我希望临终前尽可能呆在自己的家里;或者,如果比较幸运,呆在一个明亮、温馨的临终关怀机构里。我希望自己能在尽可能清醒,至少还能认识亲人的时候告别,身边有真心爱我,但不要太悲伤的亲朋。最好,我还能看到喜欢的文字或画面,听到喜欢的音乐或声音。亲朋们不必无休止的追问,我还有什么遗愿,而是和往常一样,谈些我感兴趣的话题。我不希望有一个很多人参加的葬礼,其中很多人不得不尽力地保持着肃穆的表情。我希望亲朋们在我离别后,很快地回到他们过去的生活里,跳舞、唱歌、创作、旅游,然后偶然谈起我,就像谈起一本读过的书,或是一部看过的电影。我还希望,家人们在我死后,才把我送到医院,为的是留下我身上还有用的组织或材料,在另外一些人身上,留下一些对我的记忆。我并不期盼有一个永恒的天堂,而是觉得,无数普通的碳、氢、氧、磷等原子,以无数亿分之一的概率,曾短暂地组成过我这样一个生命个体,这本身就是个和天堂的存在同样足以令人惊叹的奇迹。”这是吴海云关于死亡的畅想。
本报记者 蔡文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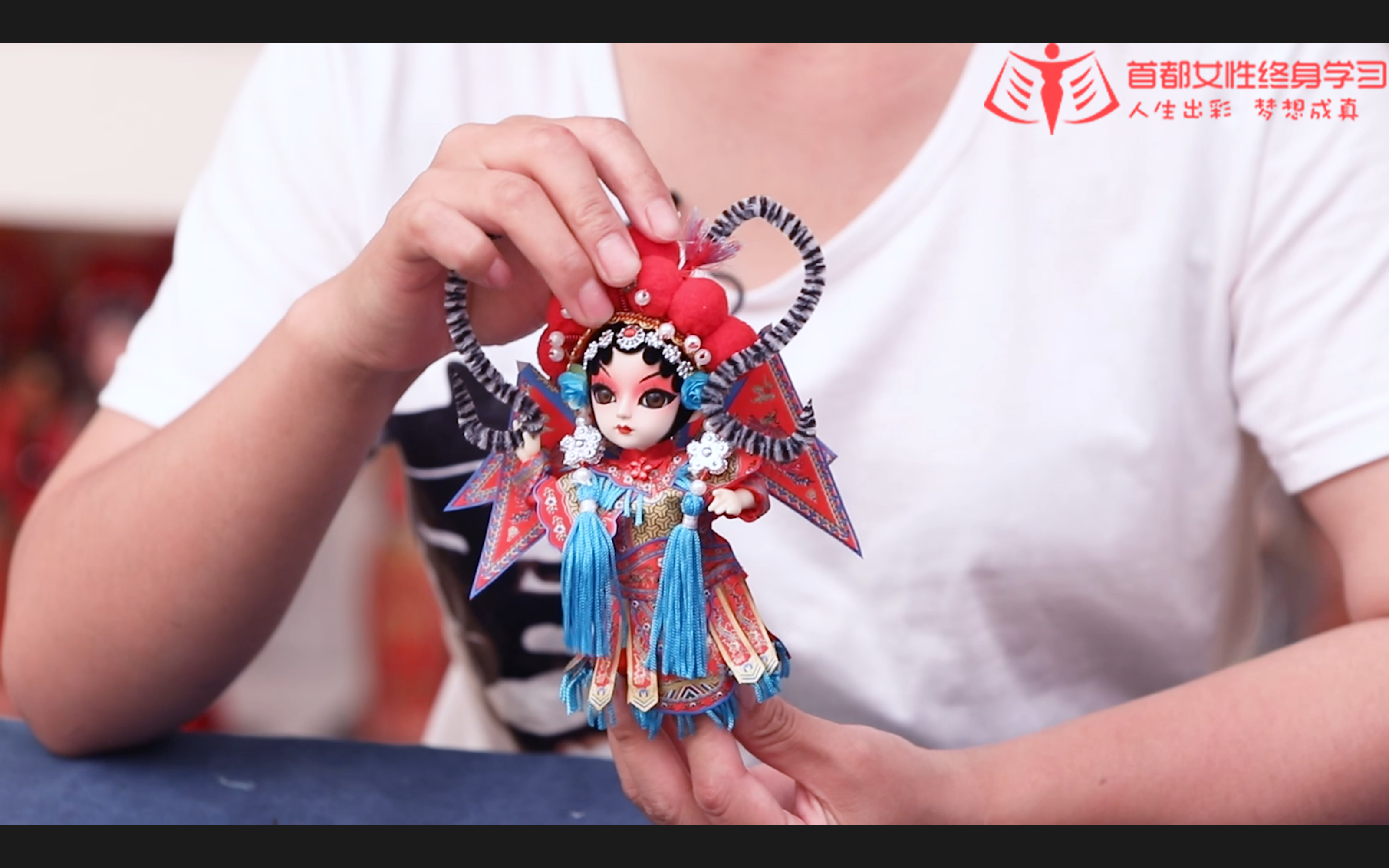



全部评论